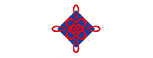8月15日,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数据。公告称,7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,但世界经济滞胀风险上升,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。下阶段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,着力稳就业稳物价,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。
作为下半年的开篇,7月的经济数据引人关注,“扩内需、稳就业”传递了哪些信号?我们又该如何审视并应对今后的挑战?日前,知名经济学者、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接受了观察者网采访。
观察者网:滕老师您好,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。7月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速只有2.7%,国家统计局今天提到“扩大国内需求”,我们此前也聊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(CPI)指数和国内整体供需关系等问题。整体而言,现在国内总需求相对不足,这从经济学上应该如何解读?
滕泰:需求起不来有多种原因。它是长周期、中周期和短周期叠加的结果。
短期影响需求的毫无疑问是疫情防控影响、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、居民消费倾向递减、房地产开发投资负增长、企业投资信心减弱等等。
7月刚公布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负增长6.4%,值得重视的是这个数据能好转吗?从比较长的周期来看的话,目前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已经处于一个下行期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(Simon Smith Kuznets)提出全球大的房地产基建周期一般是15~25年——也可以把它叫做“库兹涅茨周期”或基建投资周期。我们取中值的话,那就是20年。2000-2020年是中国房地产和基建的上行周期,那么2020-2040年就是一个下行周期。目前来看,相对而言中国房地产和基建总体过剩,短期内大规模修建新项目的需求很少。可能再过20年,很多房子、道路老化或者废弃,需要大规模更新和修建,那时房地产和基建才会再次进入下一个上行周期。
基建周期进入下行周期,它带来的需求收缩是巨大的。中国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55万亿,新增资本形成在114万亿的GDP中占比超过40%,欧美发达国家是20%多,印度是27%。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的角度来看,未来10年如果中国房地产基建在GDP的比重从40%以上降低到25%以下的话,那么投资增速的放缓就是可想而知的。
可能个别年份固定资产投资是负增长。这种情况下,它带来的需求减少不是短期的,而是长期的。这也就是说,跟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相关的产业链上的建筑、建材、钢铁、水泥……这些需求增速长期趋于放缓,这是长周期带来的需求收缩。
从中周期来看,现在也是制造业投资的收缩周期。制造业的厂房设备投资周期,也可以把它命名为朱格拉周期(Juglar cycle)。朱格拉(法国医生、经济学家)观察到了经济有9-11年周期波动。实际上,这就是厂房设备更新换代的周期。
在中国高度的、快速的工业化以后,它要走过一个阶段,在下一个阶段才会迎来大规模的更新换代。目前来看,中国很多厂房、设备现在无须立马推翻重来。从制造业厂房设备投资周期来看的话,未来一段时间内,恐怕也是个收缩周期。
从3-5年的库存调整周期来看,现在是去库存周期,它也是下行的。相对而言,我们总体是生产过剩的,而不是供给不足。
金融周期是信贷收缩与扩张所带来的周期。现在来看,全球金融处于收缩周期。美国和欧洲都在回笼货币,资本市场在下跌,它的金融周期是收缩的——现在中国谈不上是收缩,但是它也不处于扩张周期。目前我们金融周期对需求的支撑作用,可能也是不够的。
此外,今年二季度人民银行的储户问卷调查显示,倾向于“更多储蓄”的居民占58.3%,这比上季度上升了3.6个百分点,倾向于“更多投资”的居民占17.9%,比上季度下降了3.7个百分点。居民储蓄存款意愿边际上升,投资意愿边际下降。
这就是说,在我们经济和收入增速出现下滑的时候,大家的储蓄增速居然是提高的。这也会带来总需求的收缩。
因此综合来看,当前中国的需求下行,既有长期的房地产基建周期下行因素,也有制造业厂房设备投资周期“高峰已过”的原因,同时还有金融扩张力度不够、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、消费倾向递减和整个社会平均利润率下滑、疫情防控等等影响因素。
观察者网:在海外需求方面,我们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?
滕泰:现在还没出现。从2020年6月份以来,海外需求一直是支撑中国需求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,出口一直在高速增长。
欧洲、美国,这些国家稳增长的路径跟中国不一样,中国重生产、重投资、轻消费;欧美是重消费,轻投资,生产是由企业决定的。他们2020年以来稳增长的方式是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,财政政策大规模发钱。
欧美从2020年6月份开始,消费变成正增长,可生产又跟不上,他们就只能大规模进口中国商品。
欧美重消费、轻生产,它的副作用是拉升通胀。为了控制已经创40年新高的通胀,从今年3月份开始,欧美都在回收流动性,大幅度加息,经济衰退风险已经越来越近了。一旦下半年或者明年欧美陷入经济衰退,中国出口表现难免要下降。这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。
观察者网:通过一些报道也能看到,现在欧美的库存积压问题开始隐约显现了。
滕泰:这个值得高度重视,因为一旦欧美需求回落,肯定会影响到中国出口。
很多人把中国的出口增速跟人民币汇率挂钩,认为汇率一升值,出口增速就掉下来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把过去20年中国出口增速的波动,和汇率做一个相关性分析的话,两者是没有明显相关性的。人民币汇率从8.3升到6.3的时候,我们的出口其实一直都是高速增长。也就是说,中国出口表现,跟汇率的相关性不大,反倒是跟欧美需求的正相关性极其明显。
欧美经济复苏,中国出口就大涨;欧美陷入衰退,中国出口就要遭遇下行压力。2008年的次贷危机、2010年的欧债危机,都影响了中国出口表现。如果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欧美陷入经济衰退,中国出口面临的压力可能超乎想象。
观察者网:说到出口贸易,中美关系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。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,佩洛西近期又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,窜访台湾地区。多年来美国的一意孤行让中美关系走向紧张,在经济方面,这提醒我们今后更应该要警惕哪些问题?
滕泰:美国最近要推进通过芯片法案,一定会对中国的相关供应链造成冲击。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也会造成负面反应,并对企业家的信心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产生负面影响——这对双方都不利,但是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会更大一些。
长期以来,中国的出口表现拉动了国内生产。中美紧张关系影响的不仅仅是出口预期,还有企业家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:如果大环境不稳定、不确定性在增加,那么企业就会趋于保守,信心收缩。目前来看,除了台海局势,我们还要关注拜登政府所谓的联盟策略带来的挑战。
现在北约在美国授意下邀请日、韩参加,让北约向亚太地区延伸,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军事组织;美、日、澳在打造所谓“军事同盟”;佩洛西跑到亚洲来,要和日、韩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构建所谓的“共同利益和价值观”;同时,美国也在加强跟东盟和印度的经济联系……美国在试图打造的这种同盟策略,会给我们的外交、经贸带来巨大挑战。中国面对的外部挑战不是在一个棋眼,而是整个亚太板块,以及全局性的外部环境变化。
观察者网:需求不足和预期转弱,它既有经济因素的直接作用,也受国家外交、地缘政治等多方面环境影响。面对内外挑战,您觉得今后要关注哪些方面?
滕泰:以前我们讲预期转弱,它是内部的,是社会平均利润率下滑造成的。现在不仅仅是这个问题了:台海危机、美国联盟策略、欧美从高通胀转向经济衰退带来的不确定性……经济的、非经济的条件综合到了一起。
经济政策需要深度转型,最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是提振消费。
今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为3.3个百分点,贡献率为69.4%,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到2/3了。如果后面的稳增长工作全是从投资的角度下手,这很可能是不合适的。“该修的路、该修的桥”都修完了,有效投资的空间就慢慢变少了。要想把经济搞好,今后一定要重视消费,下定决心:不要总盯着投资和生产,而是要重视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、降低利率,以提振消费。
去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5.4%
第二个就是重视服务业。从二季度数据来看,GDP比上年同期增长了0.4%,其中第一产业(4.4%)、第二产业(0.9%)都是正增长,但服务业是负贡献(-0.4%)。可以说,现在受打击最严重的就是服务业。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。
国家统计局之前发布的数据显示:初步核算,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4.2%,二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8.8%。服务业差不多是制造业的两倍。服务业不复苏,从供给面上来看,经济就好不了。
服务业是大头,所以一定要稳服务业。一方面我们要明白,服务业的发展不是压制制造业,它是支持制造业的。服务业的发展是推动制造业发展最大的动力:教育培训为制造业提供人才,科技研发为制造业提供新产品,商业物流促进制造业分工越来越专业,广告传媒为制造业打开市场……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帮助,如同制造业对农业的帮助一样。
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科技发展,农业占比已经降低到了7%,但是我们农产品产量提高了,占比下降又有什么关系呢?反过来看:2001年,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.22%,2021年为53.31%。中国服务业占比提高的20年,就是中国制造业成为全球龙头的20年。
只要制造业的科技生产力发展了、产量和技术提高了,内部占比降低了无需过于担心。站在全球竞争力、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,其实中国服务业占比的提高,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指标。多年来,服务业占比一路涨到54%,帮助中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,以后还会提高到60%、70%,这才是正常的经济结构升级。
另一方面,服务业对解决中国的就业压力也非常重要,中国后面会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,年轻人的失业率来到了历史新高,这个要引起高度重视。就业问题不可能单靠制造业来解决。伴随着工业机器人的发展,不用几年,中国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会从现在的2.3亿降低到2亿以下,释放大量的剩余工业生产力——农业也一样。伴随着科技进步,可能十几年后,一亿农业劳动人口就完全可以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。
随着工业自动化技术的提高,工业产量不但不减少的情况下,它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,游离出来那一部分就是“工业剩余劳动力”,其边际产出是0,农业同理。这些农业和工业剩余劳动力,只能靠服务业的发展来吸纳。
长期以来,我们有几个错误观念:第一个是重生产、轻消费,认为生产是创造财富,消费是浪费财富。忽视消费、消费疲软,最后就导致需求不足、生产过剩、经济下行;第二个就是重物质财富,轻非物质财富。认为制造业是创造财富,服务业是财富再分配,这种观念其实是错误的。
服务业本身就是创造财富——哪怕它跟制造业没有关系,小到理头发这样的服务业,它本身也有价值。往大里说,美国的文化娱乐产业,如百老汇、好莱坞、迪士尼,它们都直接创造了大量非物质财富;再看电子信息产业,不但占美国GDP的比重高,而且引领全球经济发展。
观察者网:刺激消费也好,大力发展服务业也好,背后有一个核心问题是居民收入。比如居民收入过低,自然就会抑制消费需求,导致老百姓“越没钱,就越要存钱”,这反过来会加剧需求不足的压力。对于这个问题,您是怎么看的?
滕泰:从宏观上来看,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在下滑,以前是8%,现在掉到6%甚至4%以下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在下滑,毫无疑问它会带来影响。阶段性地来看,它跟中国现在受疫情冲击也有关系。我们国家也重视这个问题,也提出要实现“共同富裕”。
现在我们回顾过去的20年,从按要素分配的角度来看,初次分配环节确实有些问题需要改进,比如某些部门并没有创造与回报相匹配的价值。创造财富的五大要素是劳动、土地、资本、技术和管理,它们共同创造了经济增长的“蛋糕”。但是土地部门和金融部门依靠垄断或者是人为制造的稀缺,获取了超额的要素报酬,挤占了另外三种要素应得的要素报酬。
从经济学上来讲,未来要想增加居民收入,就要增加劳动者、管理者和技术者的收入,减少金融和土地部门的超额要素报酬。单从经济学的理论上来看,每个要素都有它的边际生产力。按照边际生产产出、边际生产力来分配,这才是合理的。我们应该对每种要素对生产率的贡献,以及它应该获取的回报区间,有更加客观的认识。
需要注意的是,引导要素报酬合理化,不等于盲目地行政干预——市场经济的要素价格是市场供求关系主导的,比如劳动者工资也是供需关系决定的。政府要做的是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,减少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,减少金融和土地的垄断。当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更完善了,初次分配更加公平了,那么居民收入自然就增加了。
初次分配强调要素市场化改革,那么在二次分配环节呢,我们就要关注如何去使用我们的税收促进合理的转移支付。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,我们国家从高收入者和企业那里获得的税收用于基建,修路修桥搞投资。未来,我们的财政政策需要从投资性的财政政策,转向收入性的财政政策。前20年我们修路修桥,现在我们的桥、路已经饱和了,那么我们就要将钱用合适的形式发放给中低收入的老百姓。工资是劳动力市场决定的,但是税收收入如何使用,这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。
拿稳就业来说,美国的稳就业方式是给中小企业发钱,中国的选择是给企业退税,但退税本身自带一个内在问题:“缴的多、退的多”。在实际操作层面上,这可能导致一个问题:假设你的店铺因为疫情冲击,被迫关门歇业,那么这一段时间你的收入是0,那么你退的税就是0——现实中,相比于小微企业,大中型企业反倒可以从退税政策中获得不少利益,结果原本用来稳市场主体、稳就业的宝贵财政资金就变成了对大中企业的变相纳税奖励。
我们要保市场主体,今后一定要关注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,重视普通劳动者。这可能还要涉及一个观念的转变:我们不能认为给老百姓发钱稳消费就是“打水漂”。对于增加居民收入、提振消费,支持服务业尤其是实实在在地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,我们应当给予更多关注。
- 首 页
- 纺织资讯
- 2026-02-05 聚力专精特新 共筑产业未来—2026中国纺联春季联展【纺织专精特新专区】即将启幕
- 2026-02-04 链接全球家纺商机,2026intertextile秋冬展展位开启预订!
- 2026-02-03 数读2025 | 盘点全年中国纺织行业对外贸易表现
- 国内展会
-
海外展会
- 会员天地
- 对外投资与贸易
- 纺织国际产能合作
-
党建园地
- 关于我们